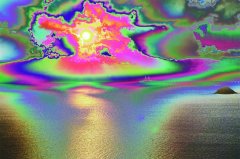武侠片与神怪片的电影种子
2023-08-17 1977 刘荒田 澳门日报


令狐昭
早期粤语片的发展可谓困难重重,有研究指香港影界为了在禁拍方言片的法令下谋求生路,才积极製作国防片以迎合国府政策,结果导致大量粤语国防电影出现。①不论此现象是“有心栽花”还是“无心插柳”,由于港英政府和南洋当局诸多禁制,一九三八年中以后,影人只能以更多的娱乐趣味作掩护,其时国防片热减退,民间故事片兴起。正如商业电影高手洪仲豪为邵仁枚的南洋影片公司摄製了国防片《回祖国去》(一九三七年)等作品后,便自立门户,与太太钱似莺招揽了有“神童”之誉的新马师曾演出民间故事片《玉葵宝扇》(一九三八年)、《孟丽君》(一九三八年)以及武侠片《方世玉打擂台》(一九三八年)。
十月广州沦陷,随着广州电检分会的消亡,国防片製作量大减。跟国防片呈此消彼长之势的民间故事片、宫闱片、武侠片,主要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和木鱼说唱文学。民间故事片虽涉及导人向善的家庭伦理或社会故事,却被评论界直斥为封建落后和低级趣味,对于抗战时期的国家民族毫无裨益。然而武侠片、神怪片、恐怖片藉着感官刺激,为深受时局困扰的平民提供临时的避难所,其兴旺期与民间故事片重叠,都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底,正是国际局势大变、中国战况急转直下、香港人心惶惶的一段日子。②百姓身处社会危难,需要民间信念的安抚、传统价值的依附,乃人之常情。
如果说第一波粤语国防电影未能达到预期效果,可归咎于香港观众“看电影怕提及战争”或“对严肃题材没有太大兴趣”等现实因素,国防理想与大众现实之间的“距离”,可否追溯至一九三六年有关中国电影走向的笔战?或者从该年“国防文学”与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之争中找到端倪?事后看来,这两个口号除了理论资源不同、侧重点稍有差异,其实都是指向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。紧接着的文学思潮纷争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进入高潮,其间梁实秋重提其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观点、老舍代表“文协”指出“目前一切,必须与抗战有关”、张天翼的讽刺小说《华威先生》引起关于“暴露与讽刺”的论争等。香港在地理上虽然远离论战中心,却势难不受其政治气候与文化辐射影响。
广州沦陷致使大量内地人士把国难经验具体化并带到香港,民众终于体会到失去家园的危机。加上华南文化中心转移,歌伶义唱筹款及灌录抗战歌曲,粤剧界亦创作了不少爱国题材剧本。这些文艺产品既能宣洩对敌军的不满,又可教育大众认识国家和战争,填补了民众思想基础的“空白”。不过战时由“政治之力”促成的文艺大众化很容易演化成文艺政治化,电影的娱乐性与艺术性则被后世理解为“冲突”的两面——当时神怪片和恐怖片被卫道者视作歪风邪气,而黄岱的《锺馗捉鬼》(一九三九年)、《古墓冤魂》(一九三九年)和冯志刚的《观音化银》(一九四〇年)等作品却炮製出创造性和批判性兼具的光影奇观,无形中为这片即将沦陷的土壤播下神怪奇幻的电影种子。
本文或来源网络共享或用户投稿文章,不代表澳门新闻日报立场,转载联系原作者并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yeeea.com/yishu/3169/